

1925年,在墨西哥城的中心,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车祸。
18岁的少女和自己的男友坐上驶往家中的巴士。
女孩满面春风。
男孩深情款款。
他们望着窗外,
谈论着街上的树枝为何掉落,
谈论着那对在巷口吵架的情侣。
这一刻,在过往看来,显得如此平常。
女孩甚至还欢腾地对男孩说:
“我考上了心仪的医学院校,我简直没办法不为自己感到骄傲。”
可就在话音落地的刹那,灾难重重降临。

一辆有轨电车直冲冲撞向这辆巴士。
它凶猛如一头野兽。
直盯着那个如花少女而来。
不留情面,不留余地,只留下伤痛的喘息。
“锁骨骨折,多处肋骨骨折,脊椎骨折。
骨盆被扶手刺穿,下体穿出。”
这一声声病情通报,像一个魔爪,伸向了这个18岁的女孩。
巴士的乘客中,独独她被厄运选中。
面对痛,锥心的痛。
她说:
“就像一道闪电照亮大地,我突然生活在了一颗痛苦的行星上,透明如冰。”
她哭不出来,破碎感搅动着她的内心。
她的灵魂,在被撕裂的痛苦中分成了两半。
一半是女人。
一半是烈士。
在最后的呻吟里,她喊出了自己的名字——
“弗里达·卡罗。”

弗里达·卡罗。
一个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女子。
一双一字眉,浑然天成。
哪怕只见一眼,也足以令人魂牵梦萦。

她充满风情。
在夜色场合中,始终两颊带笑,双瞳剪水。
她性感逼人,却不单单只为男人,也为女人。

可这样的她,不是只有貌美。
还有无尽的才华。
她是被印在钞票上的女人。
她的一生画了大概150幅的自画像。

毕加索称她的画是个奇迹。
甚至,还送了几套耳环给她,以表爱慕。

众人都说,
弗里达一定是个奇才,
是天之骄子,
才能画出旷世名作。
殊不知,孕育她的是痛苦,是绝望,是分裂,是在夹缝中起舞的力量。
在人类的认知范围内,它被称为——重生的渴望。

弗里达,并不是被上天眷顾的孩子。
6岁时,她感染了小儿麻痹症。
走路与常人不同,令她感到羞愧。
她爱待在家里。
常常在窗户上画出一扇门,想象自己能逃离当下的生活。
由于从小病痛缠身,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。
直到18岁的那场车祸,夺去了她对生活的所有幻想。
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瞬间衰老。
在医院,她住了一个月的时间,纱布缠身。

在病床上,她奄奄一息。
面容沧桑不已。
那时,她的男友仅来看过她一次。
以为她快死了,便离她而去。

医生们在她的身体上到处缝缝补补。
她无力,连呜咽声都发不出来。
出院后,她在家里卧床8个月。
很少人与她说话。
很少人来看望她。
她没收到病人该收的鲜花,也没收到鼓励的卡片。
很长一段时间,她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忘。
而在这种孤寂感的催动下,“画家弗里达”悄然而生。
父母为她在床上装上一面镜子。
给她一个调色板,让她用画画打发时间。

看着镜子里反射出的自己,她有了“自画像”的念头。
在画里,她身姿坚挺,完好无损。

父亲问她:“弗里达,你在画什么?”
她坦诚地说:“我在画我自己的现实。”
就这样,在那张床上——
从春夏到秋冬,
从年头至年尾,
她画笔不辍,日日在画。
一种力量汹涌在她的心间。
如她所言:“那是来自艺术的感召。”

当她能下床行走,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画作拿给了当时的艺术界先锋——迭戈·里维拉。
“请你看看我的作品,我能成为艺术家吗?”
那时,迭戈正爬着梯子在画壁画。
他一步一步挪下身躯,盯着眼前的这个女人看。
他眼里的她,娇小无比。
好像一朵易碎的玫瑰。
她眼里的他,是一个粗壮的男人,却有一双玲珑小手。
他们的会面,夹带着激情的火花。
仿佛注定了,会催生出一场旷世虐恋。
在一座蓝房子前,迭戈对弗里达示爱了。
他们热吻。
他们上床。
爱得激烈。

弗里达的父母见了,对迭戈说:
“我警告你,她可是个魔鬼。”
迭戈毫不在意,连连点头:“我知道,没关系。”
1929年。
他们已约会近一年的时间。
迭戈迫不及待向弗里达求婚。
他手捧鲜花,向她走来。
在艺术圈内,大家议论纷纷。
在外形上看来,他们是那么的不匹配。
甚至有人用“大象和鸽子”来形容。

可弗里达感到幸福。
她爱迭戈。
更准确的说是崇拜他。
崇拜他对艺术的理解,
崇拜他对美的想象,
崇拜他的画笔,
崇拜他的一切。
在迭戈面前,她是女人,只是女人。
为爱而伤,为爱而狂。

或许是艺术家的共性。
迭戈情感丰盈,
却渐渐从多情堕落至滥情。
在与弗里达结婚前,他已离婚2次。
招蜂引蝶的本性,早已隐驻其中。
婚后,弗里达专注自己的画作。
迭戈的事业也风生水起。
可渐渐的,弗里达发现了迭戈的风流本性。
在花花场所里,迭戈与女人们谈笑风生。

在她们面前,他显露自己的智慧,人格魅力爆棚。
女人们都爱他。
为他超前的革命思想所欢呼。
为他的画作而雀跃。
剩下的,就是鱼水之欢。
从被丈夫背叛的那刻起,一种别样的情绪开始出现在弗里达的画里。
带着恨意的,
带着摧毁的,
近乎疯魔的。
而新婚第一年,接踵而至的还有命运发起的苦难在折磨着她。
1930年。
因为身体原因,弗里达怀胎3月后流产了。
悲伤还未消散,迭戈又因为工作,把弗里达带往了美国。
从墨西哥到美国定居。
弗里达以为新的环境能让自己得到疗愈。
现实却完全相反。
美国高楼林立,充满商业气息。
她厌恶城市的冰冷。
她想念起了蓝房子和温暖的墨西哥城。
那几年,她拿起画笔,画下惊世之作——《墨美边境上的自画像》。

她的画里,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情绪。
有寒夜,有暖阳。
有摩登都市的冰冷,也有文明古城的韵味。
她将情绪画在纸上,不论暴戾还是温和。
直到1932年,弗里达再次不幸流产。
她用笑容掩盖自己的脆弱。
但在画纸上,逼仄的空间里,满是对生活的怨恨。

她的画里,开始出现死亡。
其间,流动着十分黑暗的,粗粝的情绪。
同时,也有着一个女人面对苦难的勇敢。
她似乎从不逃避伤痕。
尽可能逼自己直面残酷现实。
哪怕面对第三次流产,她亦是如此。
1933年底,
在弗里达的祈求下,
迭戈终于同意与她回到墨西哥。
真正的绝望与破碎,却再次砸向了弗里达。

在迭戈的工作室,她目睹了一场偷欢。
眼前的男女,正行苟且之事。
弗里达愤恨,拿起身边的椅子狠狠砸了过去。
一个是她妹妹克里斯蒂娜。
一个是她亲近的丈夫。
“被生活谋杀了。”
这六个字,
重重坠向她的心间。
她知道迭戈出轨,可这一次于她而言是毁灭性的。
作为一个女人,她被当场撕碎。
她逃出家门,离开了迭戈。
寻到一个栖身之处,她开始画,不停不歇地画。
此后,她的画里,开始出现凶猛且悲壮的伤口。
最著名的,莫过于那幅《轻轻捏了我一下》。
满地是血,行凶之人却在法庭上,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——
“我只是轻轻捏了她一下。”

正如迭戈对弗里达的伤害是一样的。
他的出轨,
他的不忠,
他轻而易举犯下的错误,
其实都如刀割般重重划在了她的心上。
她早已碎裂,布满伤痕。
与迭戈分开的一年里,她开始勾引男人。
在酒馆里,她大口的喝龙舌兰烈酒。
姿态轻浮。
任人调侃。
当然,以她的身姿,
她的魅力,
找到一个男人上床,绰绰有余。
她与摄影师,
与雕塑家,
与音乐人,
以身体交欢。


放纵的快乐燃烧着弗里达。
这一切都让迭戈感到嫉妒。
他暴力地夺回了弗里达,将她占为己有。
弗里达从了。
爱得越深,恨得越深。
但对弗里达来说,这一切还不够。
她仍要报复自己的丈夫。
1937年,弗里达开始一段婚外情。
和一个叫托洛茨基的老头。
他是迭戈的偶像。
是众人口中的大英雄。
却同样没办法抵挡这个妖孽般的女子弗里达。

他和她开始一段私情。
弗里达不做掩饰,让迭戈看见他们的欢愉。
她终于激起了他的嫉妒之火。
1938年,11月6日。
迭戈和弗里达离婚。
这场相爱相杀的感情,终于走到落幕的那刻。
弗里达心里却始终爱着迭戈。
在收到离婚契约书的那天,她创作了《两个弗里达》。
两颗心脏。
一颗是迭戈不再爱的,一颗是迭戈曾经爱过的。
她手握剪刀,白裙间鲜血淋漓。

外人看是残酷,是痛感横生,是被伤透的心。
于弗里达来说,却是剪断这一切,期待新生。
她不再只做一个女人。
她要做艺术的烈士。
与它同生,同悲,同死。

在弗里达40岁时,灵感日日都在喷涌而出。
她对友人说:“我的画作一定会闻名世界。”
没多久,她的事业真的开始腾飞。
她被称为是墨西哥的超现实主义代表。
她似乎活在梦里。
她的画,散发着无边无际的想象。
还有,对生的渴望。
她笔下的沙漠,能肆意开出花来。
树木的根部,总是泉水涌动。

和她心里背负的痛苦不同,
她的画布上永远充斥着大块的彩色。
那是她的向往,亦是寄托。
画里有亡灵,但它的手中抱着鲜花。
弗里达在沉睡,却身披绿叶。

在她的画中,充满复杂性。
有死亡,也有生的气息。
而这种矛盾感,正是她生活最真实的写照。
她是一边流血,一边奔跑的人。
在她后期所作的画中,人们更震惊的是其中流动的悲楚感。
在作为女人这个角色中,她是受伤的麋鹿。
万箭裹腹,仍面不改色。

40年代,弗里达的作品在纽约售罄。
世界向这位艺术的烈士张开了双手。
可就在此时,弗里达再一次陷入了病痛的漩涡。
她和撕裂的痛感抗争。
命运愈想阻止她创作,她愈顽强。
病床上,她在紧身的胸衣上作画。

画中,荆棘缠绕着她的身躯。
她不笑。
也从不流泪。

她不再掩盖自己的身体。
她承认自己的破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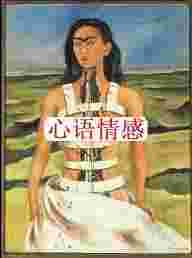
1950年,弗里达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。
一年里,她入住7次医院。
3年后,她病情再度恶化,右肢被截掉。
好友为她举办最后一次画展。
那天她得知消息后,执意坐着救护车赶到现场。
她躺在担架上,用眼睛注视众人。
那一刻,她成为了世界公认的卓越画家,一画万金。
同时,她也深深明白——身体上的痛苦,不会再持续太久了。

1954年,她被肺炎击倒,永眠于世。
年仅47岁。

这株在苦难中绽放的墨西哥玫瑰。
就此在人海中凋谢。
可我更相信——
她在死亡中得到了永生。
在时间的水流里,以最温柔的姿态,拥抱着自己。
